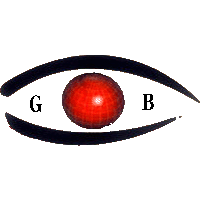历代的开垦
毫无疑问:过度的土地开垦是造成鄂尔多斯草原生态恶化的主要原因。
那么,犁铧是什么时候出现在这块土地上的呢?
据《中国历史地图集》及众多古代历史文献记载,周、春秋、战国(即从公元前841年到公元前221年)的600多年间,繁衍生息在这里的民族或部落民族有土方、鬼方、羌方、熏育、林胡、楼烦、义渠、朐衍等,这些民族都是游牧部落,他们没有开垦过土地。
而考古工作者在鄂尔多斯发掘的大量文物也证明,秦以前的历史文物中没有一件是与土地开垦和农业生产有关系的。
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期,鄂尔多斯还是匈奴族的牧地。《史记·匈奴列传》中说:“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
因匈奴是秦朝的主要边患,而这时匈奴也已经强大起来,于是战争便不可避免。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
[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徒谪,实之初县。”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迁北河榆中三万家。”
《汉书·食货志》也有类似记载:
“秦始皇遣蒙恬攘却匈奴,得其河南造阳之北千里地,甚好。于是筑城郭,徒民充之,名曰新秦。四方杂错,奢俭不同,今俗名新富贵的新秦,由是名也。”
以上几段引文,是关于鄂尔多斯地区农事开垦的最早记载。
蒙恬将鄂尔多斯的匈奴人赶跑后,在这片空无人烟的土地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移民垦殖。罪囚、老百姓,来的人相当多。从“迁北河榆中三万家”一语可以推断,“北河榆中”指今天东部丘陵山区的准格尔一带,若一户按平均4口计算,则仅迁到准格尔旗一带的就达12万人之多……全鄂尔多斯就可想而知,而这十几万人都是农民,他们必须在这里以农业生产为其生计……
于是,这块亘古以来的处女地,第一次被农业的犁铧开垦了……
当时,秦始皇除了长城、陵墓以外的另一巨大工程——南起咸阳,纵贯鄂尔多斯,北达九原的秦直道——这条古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国防大道也开始修建了……
不要忘记,这里除了数十万移民,修筑秦直道的民工,还有几十万的国防驻军,边防军的给养也就当然由这块土地的“膏壤殖谷”而供给了。
可以说,秦始皇时代,鄂尔多斯这块森林草原第一次遭到破坏,但秦朝在“迁北河榆中三万家”之后的第五年,即公元前206年就灭亡了,楚汉正在中原争霸,无暇北顾,匈奴人返回了鄂尔多斯,正在开垦土地的农民有的被杀,有的逃跑,“河套”当然就又恢复了旧观。
将近一个多世纪后,汉武帝刘彻当朝,国力强大,公元前127年后,西汉又从匈奴手里夺回“河套”,汉武帝为了控制这块土地,袭秦始皇故智:“移民实边”。
从历史文献看,汉武帝在这里搞了民屯和军屯,其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是远远超过秦朝的……开垦在新莽以后被迫停止,匈奴再次回来……
东汉光武帝刘秀也有心在这里开垦,但由于种种原因无甚作为。
其后,经过三国、晋及十六国、南北朝直到隋的三个多世纪中,活动在鄂尔多斯的主要还是北方诸游牧民族,其生产生活方式当然还是游牧,但农业在这里也一直存在,仅为畜牧业的必要补充。
隋朝在鄂尔多斯南部修了长城,约有五六百公里,民屯、兵屯导致这里人口增加,于是设了郡县……但是隋朝也短命,不到40年便成前朝旧事。
直到唐太宗李世民发兵占领了河套,文治武功,又是另一番局面了。首先,唐朝是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全盛时期。其农业生产技术和规模已达到空前的水平。从《旧唐书·宪宗纪下》中记载的一件小事,右卫大将军田缙在镇守夏州时“私用军粮四万石”,可以看出当时鄂尔多斯的农业生产规模,“私用”只能是九牛一毛,而这“一毛”竟是“四万石”,所有军粮数量可想而知。
宋朝时这里是党项族的西夏之地,农垦当然不会发达。
元代的蒙古族一直是以畜牧业经营为其传统生活方式的,对土地开垦有着本能的抵触,何况其热衷于南北征战,开疆拓土,不可能有兴趣在自己的土地上开荒种地。所以,从秦开始在这里断续的开垦完全停了下来,元退出大都后,鄂尔多斯部不久即据有“河套”,明朝也就无力去开荒了。
清朝初年是决不开荒的。首先,是出于政治需要。据有整个河套地区的蒙古鄂尔多斯部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不仅历史上就以桀骜不驯的尚武精神著称,就是在元朝灭亡后尚有余勇可贾,一直是明王朝无法平息的边患和嗣后崛起的满洲部落难以制服的对手。后来,即使在鄂尔多斯部臣服清朝后,清政府对其的戒心仍在……清初在“治蒙”问题上的手段确实是高明:他们将鄂尔多斯部分为七旗,对王公台吉以优厚的待遇,但另一方面,对其实行严密封禁,三面黄河,一面边墙,又在边墙北划出宽50里的黑界地无人区,禁止鄂尔多斯部与陕北、晋北的汉人接触,划为七旗的蒙民不能越界放牧。
清初在鄂尔多斯实行封锁政策的同时,严格禁止在盟旗领地范围内的任何开荒,蒙民招垦或者汉民越界擅自开荒者,将受到十分严厉的惩处。
但是,经过顺治、康熙前后近50年的治理,清王朝强大了,对鄂尔多斯蒙古部的封锁与控制也随之放松了。于是,在这块土地上绝迹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犁铧又疯狂了起来。
清末民初的开垦
完全可以说,使美丽的鄂尔多斯草原生态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主要原因,是清代末年和民国年间的垦殖。
虽然对鄂尔多斯森林草原的垦殖从秦就开始,在到清康熙的近2000年中间时断时继,或兴或衰,甚至出现过汉唐两代的大规模垦殖,但鄂尔多斯的生态还并没有受到致命性的摧残,因为虽不断有垦殖,但从这块土地的主体来说,仍然是畜牧业经济占主导地位,且时断时续的垦殖,给因垦殖而遭到破坏的生态不断恢复的机会。在明朝天顺六年鄂尔多斯部进入河套后,这块草原又有了400多年的恢复期,蒙古族一直在这里从事畜牧业生产。
可是,随着清王朝对鄂尔多斯蒙古部封禁的解除,一场空前绝后的土地开垦终于来临了……
据归化城先农坛石碑上的记载,清代口里汉族农民到口外(指长城北)种地始于唐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是随“绿营军”的驻防而产生的现象。
具体到鄂尔多斯,最早开垦的就是“黑界地”,就是清初为封禁鄂尔多斯部而在长城北划出的那条长1000余里、宽50里的无人区。
据《乌审旗志》载:“清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诏准朝廷大臣薄朗松·腊富所奏,开垦边墙外蒙古荒野(鄂尔多斯南部)四十里,以收地利,致使砍伐禁地林木,始创农事。”
据梁冰先生的《伊克昭盟的土地开垦》一书里讲:“‘黑界地’刚刚开放的时候,凡是‘黑界地’的草场,汉族农民到那里开垦可以,蒙古族牧民在那里放牧也可以。但是,凡到‘黑界地’种地的农民,每一犋牛(定员为一人、一犁、两头牛,每年约耕种三十亩土地)每年需向盟旗交一石谷物和四束草(合五钱四分银子)。”
最早进入“黑界地”的是长城沿边的神木、府谷、怀远、靖边、定边、榆林等县的农民。由于陕北的连年荒旱,他们便到“黑界地”逃生。可是,很快就有新的问题发生,“黑界地”容不下越来越多的口里汉族农民。于是,终于有人越境进入了鄂尔多斯蒙旗的牧地。
最初,蒙古人对此肯定是抵制的。但没多久就又欣然容纳了……
因为这里边有个“利益驱使”。
本来,鄂尔多斯蒙古部在生产生活方式上多少还保留了一些氏族制的残余,比如牧场的公有,领主和部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地域上却没有什么限制。清初划鄂尔多斯六旗时,清王朝也只是指定了每一个旗的四围边界,在一个旗内,草场又是公有的。
可“黑界地”的开垦,作为领主的蒙旗第一次从汉人那里得到利益:收租金。于是,这种氏族制的牧场公有就有了危机,终于引起了旗内台吉、王公、平民、喇嘛争夺牧场……于是,在乾隆时,皇帝便给蒙古人恩赐土地。意思是蒙旗的土地都是皇帝所有的,现在却要将土地赏赐给你们,由你们使用。当时赏地名义很多,如“蒙古人户口地”“召庙香火地”“王公马场地”等等,除了皇家恩赏以外,在盟旗内还有将草场分配给个人的其他形式。
这样一来,鄂尔多斯七旗的土地所有制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就是说,土地成分不同程度地私有了。
在“利益驱动”下,王公、台吉招垦土地,平民、召庙也招垦土地。汉族农民随之遍布鄂尔多斯七旗。
其开垦规模是以前不曾有过的……
王公贵族们为维持其荒淫挥霍的生活,不断放垦土地。
平民们为了一时的利益,也在放垦土地。
本来,最初来鄂尔多斯开垦的农民都是每年的开春以后才来到他们将要开垦的草地,搭上一座简易的房子,住下来开荒耕种。一到秋天收割了庄稼,便又回到他们的原籍去。因为当时清王朝的制度不准外地汉人在蒙旗留居。但是,随着土地开垦的深入,汉人便慢慢凭着各种理由通过不同的方式设法在蒙旗留居下来。
“雁行”的习俗就这样被打破了。
这样,也就很快改变了原先鄂尔多斯居民民族成分单一的局面。
中国近代一系列与西方列强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闭关锁国的清王朝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其中有一项,就是外国传教士的大量到来,鄂尔多斯被比利时的“圣母圣心会”等划为主要传教区,碧眼金发的洋教士在草原上乱窜,他们建教堂,收买草场,发展教民,包揽诉讼……在义和团时,鄂尔多斯掀起过一股规模宏大的反洋教斗争,杀过一些传教士和教民。所以,在《庚子赔款》时,各旗赔款数量之大是惊人的:达拉特三十七万两、鄂托克八万四千两、札萨克一万四千两、准格尔旗二万七千两……
王公们无法拿出这么多银子,除交一部分现款,用牲畜顶一部分外,全拿土地做了抵押。
这样,鄂尔多斯又有一大片土地被洋人霸去垦殖。
更大的开垦还在后边。
清王朝——这个统治中国两个多世纪的封建王朝在内忧外患之下已经是风雨飘摇。
一些有识之士便幻想来补这个天。
贻谷,就是其中一员。
贻谷是满洲镶黄旗人,曾任兵部侍郎,后来当了边疆大员。他亲身经历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的惨痛事实,一心想使清帝国富强起来,便身体力行地进行改革。据《贻谷传》记载:“复以时创设陆军,置枪炮器械,筑营垒,兴警察,立武备陆军学校及中小学校数十所。创工艺局,妇女工厂。资送绥远学生出洋,或就北洋学堂肄业。建设兴和、陶林、武川、五原、东胜五厅,练巡防马步十营,修缮绥远城垣,浚城外沟渠、建筑蒙地邨屯、植树造林、劝课园圃果实蔬菜。暇辄就田间耕夫妇问疾苦,或策单骑驰营垒,召士卒申儆之,教之以习勤崇俭,戒嗜好,勤勤如训子弟,不率者乃罚谴之。”
可以看出,贻谷确是一个清朝领导集团中头脑清醒、积极进取的人物。
而正是这个人,为晚清政府效命,在内蒙古西部搞了一次空前的大放垦,史称“贻谷放垦”。
清代在伊克昭盟地区大规模地垦荒。一方面,在沿黄河两岸有浇灌条件的前、后套大片大片地开荒种地;另一方面,毁掉了大片的以天然柳湾林为主的灌木林和乔木林,使伊克昭盟南北两大沙带渐趋相连,大大加快了伊克昭盟地区沙漠化的进程。
“贻谷放垦”因触动了蒙旗王公贵族和汉族移民的利益,受到了激烈的反抗甚至武装斗争,但这一次,鄂尔多斯的土地却被开垦殆尽……
这次放垦对鄂尔多斯产生的巨大影响直至如今,甚至将来……
贻谷最终被革职发配,清王朝负了贻谷一片苦心。
代之而立的民国政府,在鄂尔多斯的垦殖问题上继承了贻谷的衣钵,对这块土地进行了更为疯狂的垦殖……
绥远都统蔡成勋垦殖;傅作义垦殖;阎锡山垦殖;陈长捷军垦。
其中,抗战时陈长捷的军垦连王公台吉的祖坟地和成吉思汗陵的禁地也开了,结果,引发了震惊全国的“三·二六事变”。
总之,鄂尔多斯在经过晚清和民国的开垦后,森林草原的美丽景观永远消失,地理景观已与今天看到的情形大致无二了。
新中国成立后的三次大开垦
如果说历史上的过错让人徒叹奈何,那么,现实里的失误则叫人痛心疾首。
鄂尔多斯,这块历史上曾经美丽的草原,经过历代统治者的滥垦滥伐已经是百孔千疮,可是,谁又曾想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里又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开垦。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一再颁布在牧区以牧为主,禁止开荒,保护牧场的政策,但地方执行上却左右摇摆。
1957至1958年的“大跃进”浪潮中,因片面理解大办农业,全盟第一次大开荒。
1960至1962年的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全盟再次大开荒。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牧民不吃亏心粮”的错误口号下,长官意志不顾客观实际,强迫牧民开荒种地,一时,鄂尔多斯遍地牛犋,到处是锨镐并举的开荒的人们……
三次开荒累计面积66.67万公顷。
如果这66.67万公顷土地成为良田,还可聊以欣慰,而实际情形却远远不是这样。
以1960至1962年的那次大开荒为例:1960年是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中最困难的一年,吃粮问题成了全国的大问题。伊克昭盟农民的口粮标准已由年均230公斤降至180公斤,牧民的口粮标准,月供10公斤降至今7.5公斤。实际上有不少旗县社队还远远达不到这个标准。
怎么办?
这年3月份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发了一个文件,要求伊盟用开荒来解决粮食问题。
4月份,伊克昭盟地方领导在新街召开了专门研究开荒的会议,落实内蒙古党委下达的开荒指标。
群众和基层干部这时因吃粮紧张,都想在大田地里多抓一把。何况这里的农民有开荒种田的传统习惯,平时禁止开荒还有人偷着开,现在好不容易上边放了话,所以积极性很高,个个惟恐落后。
全盟马上投入开荒的劳力近7万人,牛犋5000多犋,还有拖拉机等。全盟从东到西、从北到南到处是开荒的牛犋和人群……
上级领导一看,认为这里开荒的劲头不错,又给追加了开荒的亩数。
但是,问题随之就出现了。
——宜种植的地方开了,不宜种植的地方也开了。
——农区农民有的抛下门前的土地,赶着牛犋到二三里外的牧区开荒。这样,造成了农挤牧,牲口没处放养。
——开荒的农民大部分是汉族,放牧的大部分是蒙古族,一下子开荒几百万亩,使牧场缩小,牧民很不满意,并与开荒的农民发生了摩擦与冲突。
这年,伊克昭盟共开垦20万顷荒地。
尽管地方政府反复强调开荒要做到开一亩种一亩、保收一亩,但终因天旱而事与愿违:
乌审旗新开的土地播种后缺苗断垄非常严重,有很大一部分土地的苗死光了。
准格尔旗开荒2.67万公顷,能播种的仅1.67万公顷,且不能保证有收获。
鄂托克旗开荒最多,但因天旱大多无法下种。
三次大开荒全盟累计面积66.67多万公顷,而土地的沙化面积却达到35000平方公里,比第一次大开荒的1957年的16446.5平方公里(中国科学考察院1957年测定),增加了一倍多。
天然牧场开垦后,由于原土地肥力,当年亩产数十斤,但二三年后较肥的表土已被吹走,亩产就急剧下降,最后连种子也收不回来,只好撂荒,再开垦新地。如此重复,致使撂荒地面积成倍增长。因缺少植被保护,在风的作用下很快变成沙化土地和沙源地。
严重的沙化加上干旱少雨,使周期性的大旱由时隔10年一次变为时隔6年一次。1971年到1973年甚至出现了连续3年的大旱。
全盟36.67多万公顷的耕地,每年平均有15.33万公顷遭受风灾、旱灾,补种、毁种3至5次。沙化严重的社队最多补种达7次之多。
就是这样的反复补种,每年平均有8.67多万公顷粮田基本无收成,占总耕地面积的1/5还多。全盟粮食产量低而不稳,总产量一直徘徊在1.75亿公斤左右,比1956年减产2500多万公斤。
1973年,全盟3567个生产队缺粮,占全盟生产队总数的72%,缺粮人口达50万人。
由于草场沙化、退化,使畜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突出。
牧业生产发展极不稳定,一遇灾年更是大幅度下降。
1965年的大灾使全盟牲畜头数由647万头(只)下降到463万头(只),之后,多年来牲畜头数一直在450至500万头之间徘徊。
牲畜质量下降更为明显,鄂托克旗的珠利公社,1964年交售给国家的菜羊平均每只12公斤,到1973年下降到平均每只7公斤,出现了“一张报纸包一只羊”的可怜景象。
沙化重灾区的社员生活困难,1973年农村社员的人均年收入只有52元,入不抵出的社队共有3437个,占当时全盟生产队总数的71%。
三次大开荒劳民费力、毁了牧场,造成鄂尔多斯的严重沙化……
人们本来是想通过开荒造出田来收获粮食,而结果不仅事与愿违,连原有的农田也沙化了。
人不尊重自然,自然就叫人吃尽苦头。
游弋的羊群
蓝蓝的天空,碧绿的草原,
清清的湖水,洁白的羊群。
这是——
我的家,我的天堂……
蒙古族著名歌手腾格尔曾经在这首名为《天堂》的歌里深情地咏唱过他的家乡鄂尔多斯。
历史上鄂尔多斯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曾经使这里成为牧人们的“天堂”。
让我们在此做一次简单的回顾吧。
西周时期的北方游牧部落戎狄靠狩猎和畜牧业在这里生活。
春秋战国时期的林胡、楼烦也因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的良好条件在此繁衍。
秦之后,白羊、楼烦等族从阴山北重返鄂尔多斯。匈奴冒顿单于光骑兵就有30多万,很多万匹就来自这里。
在汉代,这里“人民炽盛,牛马布野”,汉武帝请匈奴休屠王的儿子为他养马,封他为骑都尉,官至光禄大夫,这里的牛马是“衔尾入塞”。
公元391年,大夏国被北魏拓跋珪一次就虏获了“名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万余头”。
北魏占领这里后,这里被划为“河西牧苑”,其中的敕勒人已采取打“耳记”、烙“畜印”等先进的“记识”办法。由于畜牧业高度发展,出现“马及牛羊遂至于贱,毡皮委积”的状况。
隋朝时期,居住在这里的突厥人的畜牧业成为突厥汗国的经济支柱。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突厥的沙钵略可汗入侵中原,一次就调集骑兵40万。
唐代在这里设有群牧使,专管官办养马业。
宋代从北边购买的马匹,大多都来自这里。
元代,这里是忽必烈第三子安西王忙歌剌的领地。这一地区南部的察罕脑儿(今乌审旗境内)安置了4000户牧民从事畜牧业。察汉脑儿是元朝在全国官办的14个大牧场之一,以牧马为主。
明代中叶以后,蒙古鄂尔多斯部驻牧河套后,畜牧业更是繁荣。公元1570年,阿拉坦汗和明朝最后达成和议,蒙汉之间的“互市”贸易扩大了,在长城沿边一带,设立了13处大的互市场所。
清中叶,由于畜牧技术和蒙汉贸易,畜牧产品除了牲畜外,皮张、绒毛也进入交易市场,促进了牧民的生产积极性,畜牧业发展也很快……
但是,清末直至民国,这块草原上的畜牧业开始走向了衰落,主要原因是由于农垦造成的。草原被大面积地开垦,牧业的空间就小了。而在一般情况下,畜牧业是具有排他性的,放牧的地方就不能种地,种地的地方就不能放牧。
以民国年间为例:
准格尔旗以务农为主,畜牧成为副业。自民国十五年后,连年干旱,水草缺乏,牲畜死亡过半,居民每户养牛二三头、驴一二头、羊十数只。较富裕者也养少数骡马驼等牲畜。全旗约有牛5000头、驴4000头、羊40000余只,山羊较多,马3000余匹,驼、骡各七八百头。
达拉特旗牧地以柴登滩及五大仓圪泊、合义公、孙家圪泊草滩较好,养马二三百匹的仅三四户。养驼、牛数十头,羊三四百者甚少。普通人家养羊数只,牛、马一二头。全旗共有马3000匹、牛5000余头、羊10000余只。驴1000余头、驼300余峰、骡100余头。
鄂托克旗地面广大,随处可以放牧,是鄂尔多斯的主要牧场。其在往昔,养羊万只、马数千匹、驼数百峰、牛千余头者,不下20余户。普通之户,亦均养马十余匹至数百匹,羊数百只至千余只。民国十七年(1928年)后连年大旱,水枯草死,牲畜饿死者大半。此后养畜最多者马不过三四百匹,驼不过百峰,牛数百头,羊千余只。普通户一般养牛、马、驼数头,羊百余只。全旗共有羊40万只、马2万余匹、牛1万余头、驼5000余峰、驴3000余头、骡500余头。
从以上三旗的情形看,可见这里至民国年间畜牧业已经开始走向衰落。
鄂尔多斯传统畜牧业由盛到衰的主要原因是,历代的滥垦滥伐,造成牧场退化,土地沙化。而造成土地沙化的原因除此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
回答是肯定的。
杰弗·利恩在论述荒漠化的成因时,就曾明确地指出,过度的放牧是导致土地荒漠化的四大主要原因之一,“过度的放牧毁掉了以防止土壤退化的植被。”
盛极必衰,这是世间一切事物发展的规律。鄂尔多斯的传统畜牧业亦如此。
牲畜要吃草,这和人要吃饭的道理一样简单。鄂尔多斯的牧场再辽阔、再丰美,也必定有个限度。就像一条再大的船,它也有它最大的承载量一样。
远的不说了,让我们看看1949年以来近50年的情况吧。
据可靠资料,1949年,伊克昭盟全盟的大小畜总头数是170多万头(只)。而1996年全盟大小畜的统计数是735万头(只)。
牲畜数量增长了这么多,而草地呢?
据1982至1985年伊克昭盟草地资料调查,全盟草地总面积是556万多公顷,其中天然草地总面积是476万多公顷。而1949年,全盟的天然草地总面积是675万多公顷。由此可见,这里的草场不但没有增加,反而缩小了不少。
虽然新中国成立以后搞了一些人工草地和改良草地,但到如今,这里的牲畜的可食饲草仍然有80%来源于天然草地,在西部牧区可达90%以上。也就是说,伊克昭盟的畜牧业生产仍属于草原畜牧业阶段。
据专家测算,目前,全盟年产可食饲草总量大约在62亿公斤左右,按理论载畜量最多可承载460万左右绵羊单位。可现在的大小畜总量却是735万(头)只。
超载了多少?
而超载就意味着草场退化、沙化。
草地质量下降的情况也很严重:1949年,伊克昭盟的典型草原草地产草量平均每亩325公斤鲜草,以灌木、半灌木为主的荒漠草原草地每亩产鲜草150公斤。到1977年,典型草原草地亩产量下降到150至225公斤,荒漠草原草地下降到50至60公斤,分别下降了40%至60%和20%至30%;多年生禾草高度由1949年的30至70厘米下降到1979年的20至40厘米,灌木由150至200厘米下降到120至150厘米,一般草地的牧草盖度减少了30%至50%。
伊克昭盟的天然草场平均每公顷产鲜草991公斤,需1.2公顷草原才能养一个绵羊单位的牲畜。
解放初每头(只)牲畜占有草场4.77公顷,到1996年每个绵羊单位占有草场仅0.73公顷,比理论载畜面积少0.47公顷。
由此可见,在“畜牧业达到历史最高水平735万(头)只”的背后,隐藏着多么大的危机和灾难!
改革开放以来,牧区一系列的改革调动了广大牧民养畜的积极性。特别是以“鄂尔多斯”集团为龙头的毛纺织业的飞速崛起,使养殖山羊成为有利可图的生财之道,牧区的草场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虽然地方政府一直鼓励牧民们要建设草原,但实际情形并不能如预期的那样。因为现实的利益常常使人丧失理智,采取短期行为。
以伊金霍洛旗为例,这个旗可利用草场面积是34万公顷,载畜量为40万个绵羊单位,这还必须是雨水充足的年份,天旱时,只能养30万个绵羊单位,而1996年,全旗实际上牲畜总头数已经达到83万头(只),超过一倍多。这主要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方面是政策和现实的经济利益调动了农牧民养畜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因为过去看牧业生产成绩主要看牲畜头数。岂不知,这样的牧业“丰收”是用超载过度、生态环境被破坏、畜产品质量下降、低效率运行作代价的。
畜量超载,粗放型的草牧场经营,还有草原建设的缓慢……已经使这块土地上的畜草之间的矛盾日渐尖锐,鄂尔多斯草原已经向世代生活在这里的牧人亮出了“黄牌”。
既然,我们已经迎来了“生态文明”的时代,我们就应该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不要再干“竭泽而渔”的蠢事,不再为一时的“大丰收”而陶醉,我们的先人生活在这里,我们生活在这里,我们的子孙还要生活在这里……难道,我们果真要把一片荒漠留给他们吗?
(责任编辑:落溪)